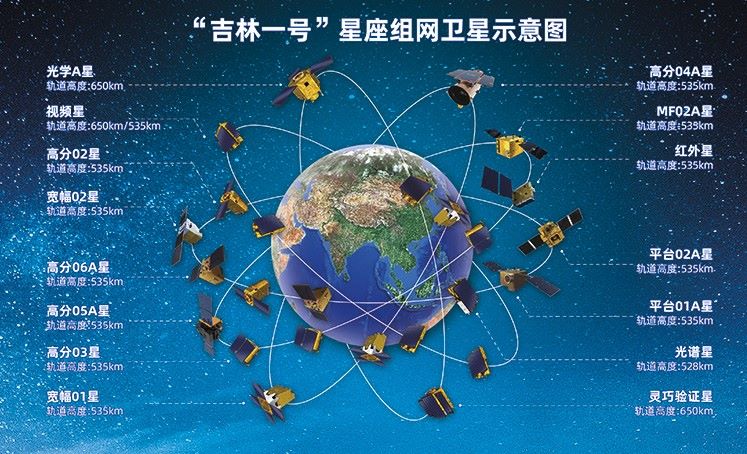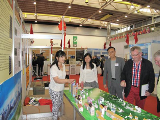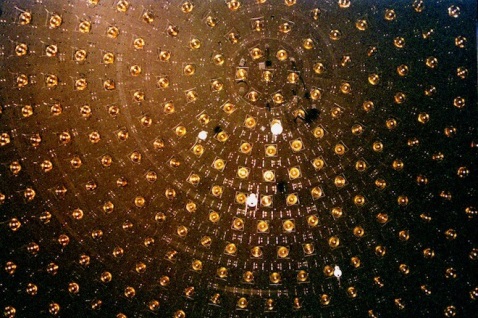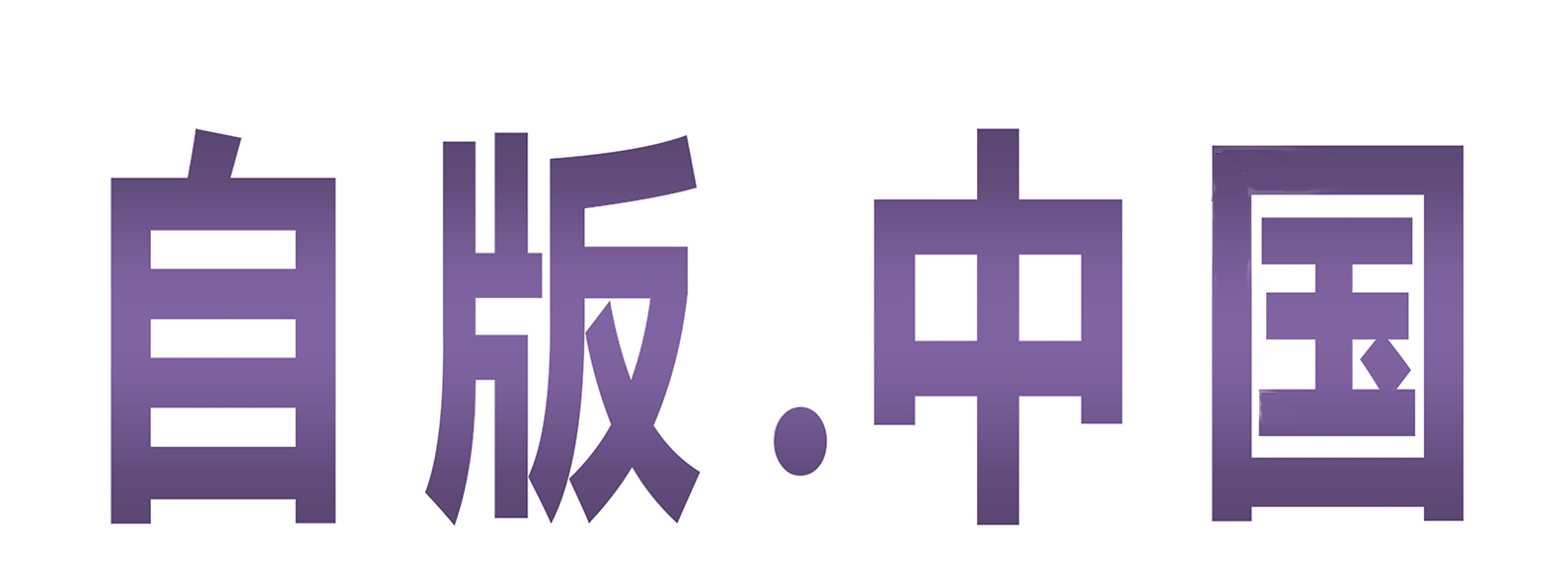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特质
作者: 马戎
2018年10月22日来源: 北京日报
作为一个结构复杂而丰富的文明体系,中华文化强韧的生命力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决定了历代的中国政体、中国人的“内”、“外”观和中国疆域的历史发展轨迹。即使在近代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中华文明体系及其特质也仍然持续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与社会演变,包括价值伦理的演化、话语体系的转变和国家体制的重新构建。那么,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是什么呢?
中华文明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道”而非个人主义
中华传统文化崇尚的是包括天下万物运行规则在内的“天道”,也被有些学者概括地表述为“天、地、君、亲、师”,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几千年来,历代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就是这样一幅尘世间人尽其才、遵守公德、各得其所、和谐有序的社会图景。
中国人坚信“天下大同”的人类理想与“天道秩序”的终极力量,认为人应“畏天命”,而在“有教无类”宗旨指导下的“教化”过程则是“天下”人类各群体感悟并接受“天道”的过程,而且坚信所有的人群迟早都应能接受这一“天道”。
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华文明不提倡个人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公德和万物众生都应遵循的“天道”,这是另一种道德伦理体系。中国人所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讲的决不是西方式“民主选举”中的多数,而是顺应天理、符合“为公而思”的公心,这种“公心”所考虑的是天下之人,不是某个派别的信众,不是某个政权下辖的国民,也不是某个小群体或个人。
中华传统文化虽然强调社会公德和集体伦理,不强调个人权利,但并非没有平等观念。中国人的“平等”观念,既体现在与异文化异群体的交流中,体现在尊重境内不同族群传统和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也体现在财产继承制度中。中原地区的财产继承是男性子嗣均分制,而不是欧洲或日本社会的长子继承制。中国人没有欧洲社会那种固化的家族“世袭”概念,不仅皇朝世系可以“改朝换代”,民众和士人可以接受那些尊崇并继承中华文化的异族统治者(亡国而不亡天下);贵胄世家也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原皇朝历代选拔贤能的主要渠道是面向全体臣民的科举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十分赞赏中国的科举制,认为比欧洲各国的爵位领地世袭制更加体现出平等精神。
直至今日,政府各级部门的领导在中国社会仍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父母官”,国内任何地区如果在经济财政、民生就业、物资供应、抢险救灾、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健、教育质量、社会保障、道德治安甚至环境生态等方面出现问题,中国国民都会指责政府部门的失职,而政府官员也会被问责。在西方国家中的政府,主要责任限于国防(“兵”)和执法(“刑”)。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道”观和民众对执政者角色功能的期望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我们在理解古代甚至今天的中国社会时,要认识到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政府之间的本质性差别。
中华文明对于内部文化多样性和各种外部文明都表现出罕见的包容态度
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既没有一神教那种强烈的“零和结构”的排他性,没有严格无神论的反宗教性,也没有基于体质差异的西方种族主义观念,对于人们在相貌、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也表现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宽容心态,甚至所谓的“华夷之辨”也仅仅是文化观念的差异,而不是本质性的区隔,所以,中华文明对于内部文化多样性和各种外部文明都表现出罕见的包容态度,但也恰恰是这种宽松的包容态度,客观上降低了周边群体的心理距离感,增强了周边群体潜在的情感向心力和凝聚力。
就社会内部而言,这种宽松的包容度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活跃和民间创造力的萌发提供了空间,使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哲学、史学、文学、医学、兵法、天文、科技、建筑、农耕、陶瓷、冶炼、丝绸纺织等领域出现了后世鲜见的“百花齐放”盛况。从中原各诸侯国“诸子百家”中衍生出儒学、老庄、法家、墨家等许多流派,许多学者跨流派互为师生,在交流与竞争中彼此借鉴、相互包容而不是强求同一,其结果反而促进了事实上的相互融合,这就是历史演进的辩证法。儒学通常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思想主脉,需要注意的是,儒学在其后续发展中不断吸收融汇其他学派的思想,始终处于演变过程之中。
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涵盖辽阔地域的政治体系。为了推动管辖区域内的行政体制和文化体系的同质性,秦朝设立郡县,推行“书同文”,加快中原各地域之间的文化融合,逐步形成以统一文字为工具载体的中华文明体系。与此同时,秦朝推行“车同轨”,统一货币与度量衡,有效地促进了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和统一经济体系的形成。汉代印刷术的出现和隋朝创立的科举制进一步推进中原皇朝管辖地域内各地区之间的文化统合。凡是实行了科举制的地区,不论其存在哪些族属语言差异,当地的精英人士都逐步融入中华文化圈。中原文明的传播地域逐步从黄河和长江流域扩展到珠江流域和周边其他地区。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各地区地理自然风貌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齐鲁、燕赵、吴越、秦、楚等不同区域的地方性传统文化长期依然得以保留特色。共性与特性并存,一体与多元并存,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另一个特质。
与此同时,在与来自“中华文化圈”之外其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中华文明先后容纳了外部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基督教等宗教及教派,吸收了外来宗教的许多文化元素,包括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制度形式和文学艺术。在文化和思想交流中,孔子主张“中庸之道”,不偏狭不极端。中华文明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老子则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正是这种主张“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理念和基本态度,使中华文化对于内部多样化和外来异文化具有举世罕见的文化包容度和融合力。
从以上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对外来宗教与文化的强大包容力,感受到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积极吸收和容纳外来文明的心态。“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用兼容并包,同仁一视,所吸收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吕思勉)。
中华文明开展跨文化交流的核心理念是“和而不同”和“有教无类”
罗志田认为,“中国的夷夏之辨……对外却有开放与封闭的两面,而且是以开放的一面为主流。夷夏之辨是以文野之分为基础的……故夷夏也应该是可以互变的”。在与其他群体交流过程中,中华文明所持的是“有教无类”的立场,采用“教化”的方法来“化夷为夏”,而不是简单地排斥其他信仰与学说,因此中国人从来没有“异教徒”的概念。由于在孔子的年代,中原地区居民的人种成分十分复杂,“所以,‘有教无类’主要不是指社会贫富等级差别,而是种族特征差别”(苏秉琦),表示对不同祖先血缘及语言文化群体施以教化时应一视同仁。在与异族交往中推行“教化”的方法是“施仁政”,“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主张以自身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德行来对蛮夷进行感召,而不是使用武力手段强迫其他群体接受自己的文化。这种政策的前提是对中华文明优越性的高度自信。“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甚至连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也强调“天子”的军队应为“仁义之师”,“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因为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和传播,所以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夷夏之辨”中的“化内”和“化外”可以相互转化。钱穆指出,“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夷夏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动态与辩证的关系。所以儒家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明确淡化“天下”各群体之间在体质、族源、语言、宗教、习俗等文化领域差异的意义,强调不同人类群体在基本伦理和互动规则方面存在重要共性并完全能够做到“和而不同”与和睦共处。
中华文明认同体系的核心是文化认同,而不是西式僵化的“民族主义”
与欧洲的文化传统全然不同,中华文明强调的是“天道”中的社会伦理与政治秩序,主张“和而不同”,领悟并遵从“天道”的群体即是享有文化素质的人,其他人群尚有待“教化”。孔子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王韬在《华夷辨》中指出:“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因此,在中华文明的这种具有高度包容性、动态化和辩证思维的认同体系中,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僵化“民族”(nation)概念。
即使晚清政府在某些形式上,特别是在与西方列强交往中表现得像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与各国互派公使并建使馆,设定国旗国歌,翻译《万国公法》,签订国际条约、设立海关等,但是在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中始终是一套传统的中华文明体系在发挥作用。
中国传统认同体系的核心是文化认同,对“天道”和儒家道德伦理的崇敬就是中国人的信仰体系。所以费正清特别指出,“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以“文化”确定群体认同和“有教无类”的主导思想。在面对内部多样性和与外部文明相接触时,“‘不拒他者’是中国的传统精神,而民族主义之类才是西方的思维”(赵汀阳)。民族主义是具有某种“零和结构”和强烈排他性的群体认同意识形态,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不可能滋生出西方式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体系。
近代以来,欧美帝国主义在对外关系中践行的是“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地缘政治中的“霸权”理念至今仍然主导着某些国家的外交思路。在今天的国际交往中,中华文明与外部文明-政体交往中遵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求同存异”的基本思路构成了中国外交活动的文化底色,使其具有不同于欧美国家外交的文化风格,赢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真诚友谊,也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大格局注入新的元素。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