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 兵
从理论研究和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当一种学说或理论在国际上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发展时,如果我们也要进行相关的研究,或者是借鉴国外的经验,首先应该做的是对国外的理论研究和与之相关的实践情况有所了解,最好是有所研究。在以往,国内随着对于“科学普及”在新形势下的更加重视,关注的焦点也从传统的科普逐渐有所拓展,拓展的方向之一,就是国际上所谓的“公众理解科学”。在这方面,前些年国内已经有了一些引进、翻译和研究的工作,但那些工作似乎主要是对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情况的介绍和研究,而对于包括范围更广的欧洲的整体情况,则仍然是近乎于一个空白点。因而,最近针对欧洲情况的研究报告的出版,就有了其特殊的重要意义,让我们可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公众理解科学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虽然国内的科普活动仍然有着传统影响的深刻烙印,但我们如今已经不再将自己只限于传统科普的范围,而将视野扩展到包括公众理解科学在内的更多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不过,这些传统和更新型的普及传播和“理解”之间,毕竟还是有着密切的关联。
可以比较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公众对于科学的支持,并不一定与公众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的水平成正比,甚至于,在欧洲一些在对公众的科学知识的普及上做得很好的国家,其公众对科学的怀疑态度还会有所增加。相反,在我们这里,在几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中可以发现,虽然公众对科学知识“达标”掌握的比较很低,但对科学表现出盲目的信仰和支持者的比例却非常之高。固然这里面有我们国内传统中对于科学意识形态化的影响,但这一正一反的对比,却说明了一个足以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现在在科学普及和传播中经常隐含着一个假定,即让公众掌握越多的科学知识,就会越有利于公众对科学的支持,而这个假定恰恰与上述调查结果相矛盾。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当下大力倡导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背后,究竟预设了什么样的目标?以及这样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或者,也可以反过来想,我们对于公众科学素养的理解,以及对于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意义的理解,是不是有可能重新反思一下呢?
上面这些,大致还是属于比较理论性的内容,而就科普图书的创作来说,又有更多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具体问题。而这些具体问题要得到解决,又同样是需要相对非功利性的基础研究的。
目前,随着政府越来越重视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对于科普工作的资助越来越大。各级政府对此都有相当的投入,而针对科普工作中重要的科普图书的出版,许多地方政府也都相应地提供资助。但相对比较有普遍性的一个问题是,这些资助,通常都是针对具体的科普图书的创作和出版,而极少有针对关于科普图书创作出版以及更一般性的科普工作的基础性、理论性的研究资助。
例如,北京市科协多年来就一直大力资助科普图书出版,设有科普创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这里,我们以面向社会征集2009年北京科普创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通知为例。在其资助范围中特别指定:
专项资金用于资助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优秀科普图书、音像制品的创作与出版。资助项目第五项规定下列情况暂不属于资助范围:学术类作品(论文、专著、译著);教学及教辅类图书、音像制品;各类工具书。
第五项的规定,将研究性的著作完全排除在外。就科普图书的基础研究来说,一方面涉及到对于研究本身的资助;另一方面,在当前的出版形势下,也会涉及到对于研究成果之出版的资助。但在上述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如此重要的基础性的科普研究,显然是不受重视甚至完全不在资助之列的。
像这样的情形其实也非北京所独有,而是有一定共性的。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从对于科普工作的更为直接的考核来说,当原创的科普图书的出版与资助相联系起来时,很容易体现直接的“成果”,成为抓科普工作的“政绩”,而那些相对学术性的基础性研究,却与这样考核的目标之联系相对间接,其作用的体现也需要相对更长的时间。不过,在基础不牢的前提下,原创性科普图书的质量又如何提高呢?仅仅只有对之直接的经济资助,甚至会有维持低水平创作的可能。
基础性研究并非只是全国性的问题,地方也有地方的特殊问题。因而,要想真正有效地开展有地方特色的科普工作,包括科普图书出版,地方政府对于基础性的科普研究也应适度考虑设立相应的资助机制,这样,才会带来科普工作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可持续地发展。
来源:学习时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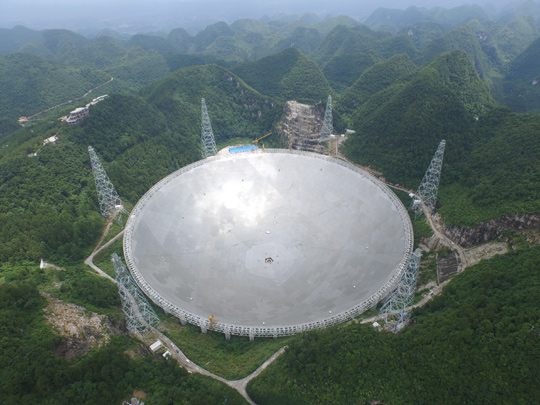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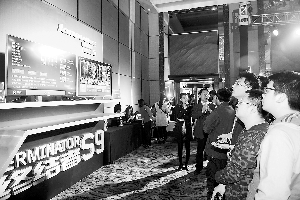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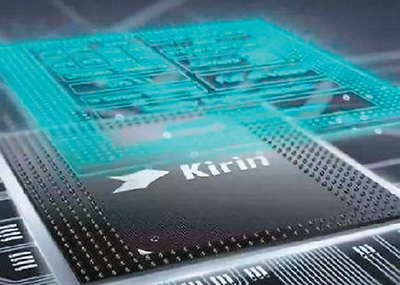
 001
001
 002
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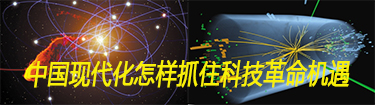 003
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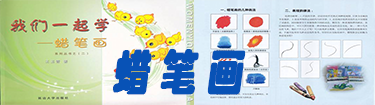 004
004
 推荐席位
推荐席位



